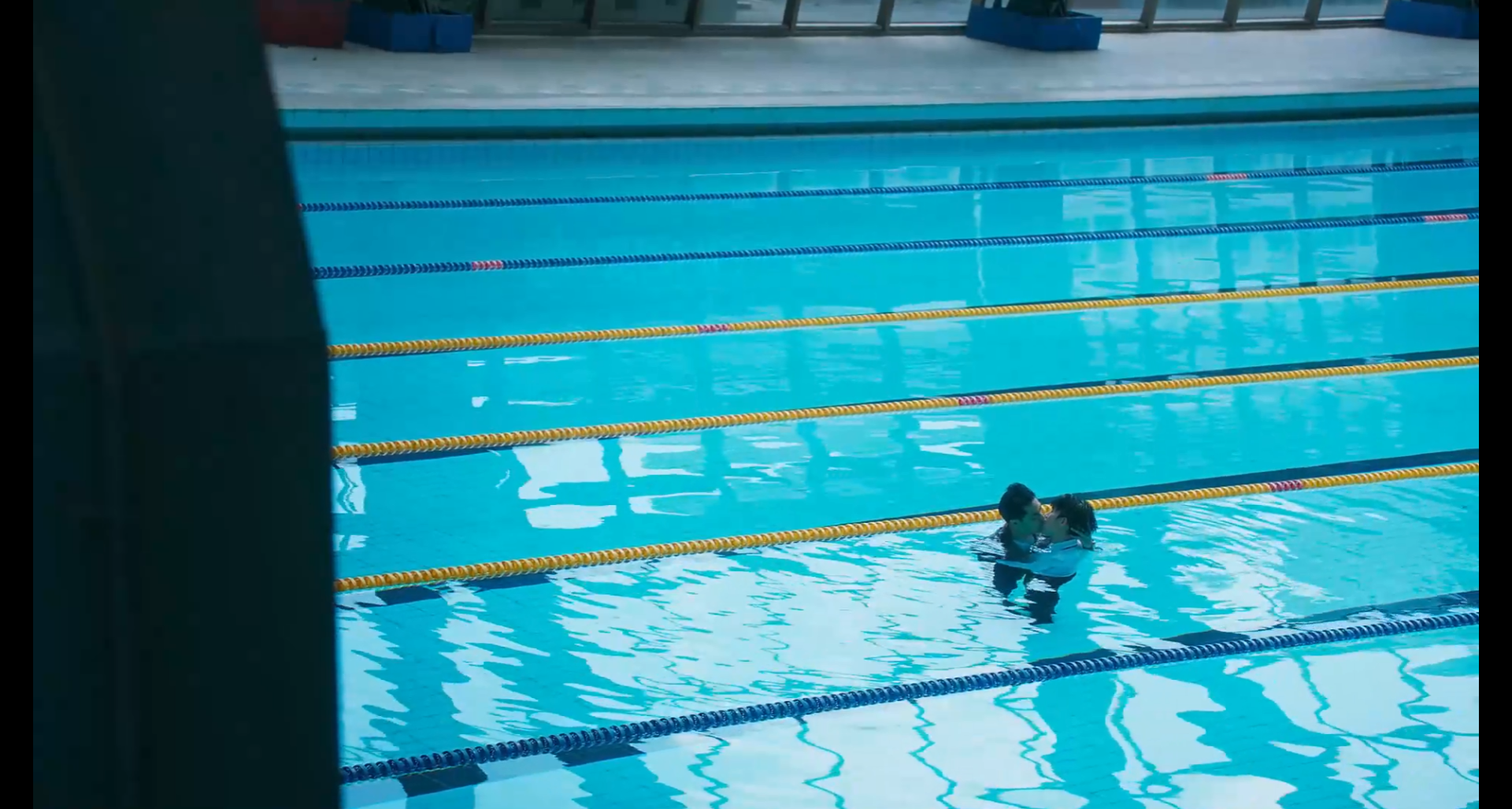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
“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,和会流泪的眼睛。”
每次听到这句歌词,其实我总会想起自己的眼睛——屈光手术是我多年的心愿。
初中的时候,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过一道桥,五百米,四五分钟的路程,我总是会在路上自言自语,说得最多的,是祈祷。祈祷家人身体健康,祈祷我喜欢的男孩子也喜欢我,祈祷我的眼睛有一天近视突然消失,又能清晰地看见世间万物。我的记忆居然时至今日还如此具体,我记得我祈祷说,“这个世界真的好美,而我这么年轻,我真的好希望,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每一天都清清楚楚地好好欣赏这么美丽的世界。”
那时候我哪听说过什么屈光手术啊,所有的祈祷与期盼,都寄托于神灵。可现在有了,大概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,这颗希望的种子就开始偷偷地在破土、发芽了。且它的生长是我对手术的极度恐惧也没能压得住的。愈演愈烈。
我下决心要做。我记得写2021的年记时我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了。我不愿意继续骗自己说:“我并没有那么需要这个手术,我并没有那么渴望。”我开始选择坦诚面对自己的想法——我只是对手术本身存在恐惧而已,除此以外,对待手术的结果,我心里满满的全都是期待。
五月末六月初,随着毕业的临近,去北京也提上日程,尤其是预答结束后较为清闲的日子,我对即将到来的去北京这件事,充满恐惧。经常在午睡的时候、在晚上临睡前、甚至在熟睡后的梦里,都堆满了害怕。睡得不安稳成了那段原本轻松的日子的常态。直到我毕业回到家,睡眠好了一些,但这份紧张也并没有完全消除。
上周末,北京的疫情突然严重了,大半夜的,我给好朋友发去消息,诉说我去北京这件事恐怕要延缓的苦恼,我很纠结,担心如果暂缓,会不会就把这件事拖黄了。那晚我虽内心不安,幸得朋友们安慰我、给我出主意,我记得大概十二点前就入睡了。第二天一早我依然决定要去北京,冒着疫情的风险也要去。因为我真的受够了这么多天的恐惧,我想当断则断,做了它,逼着自己勇敢一把冲一把。天不遂我意,起床后没过半小时就接到北京宾馆的电话,说暂停营业了,无法入住。那一瞬间我内心是喜悦、是轻松、是石头落地、是如释重负。
紧接着我又在网上查到消息说,同仁的手术要排到半年后了,也就是说我一时半会做不上手术了,急也没用。于是这一周来我终于从之前的重负状态里彻底释放出来了。头也不晕了,眼也不花了,吃饭更香了,睡觉更美了。快活似神仙的假期生活,悠然自得,快哉快哉!
就到了今天,翟主任联系我说,25号可做,但是要在他出诊的私立医院做,因为同仁排队要太久了。我又一次开始挨个征求朋友们和家人们的意见,也从中一点点分析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这过程既纠结又墨迹,墨迹到我都懒得在这描述一遍。有朋友们真好,有家人真好,你们永远包容我支持我,不厌其烦,真好。我爱你们。
晚上出去玩,一个人散步回家,走在桥上,还是初中上下学的那个桥,那个听见过我所有愿望的桥。风很大,桥上人很少,我很慢很慢地走着,发现已经好久没有独自在这么安静的情况下散步了。“我这里好安静哦,想听你说说话”。不想说得像情话,于是我发了个消息说“我这里,还真是挺安静”。然后锁屏,吹风,走路,捋清思绪。我想搞清楚,掩盖在我极度的恐惧之下的,我自己的真实想法,到底是什么。
“我要做,即便害怕。我真的要做。”
“其实我也会害怕啊,我也不是那么勇敢啊,好想也有个后背让我躲一躲。”
到家后又跟爸妈聊了好久,他们一致的态度是支持我做,支持我越早做越好,且我们一致认为其实没什么好担忧和顾虑的。
我刚才还跟一一说,想写点什么,又觉得写出来也都是无病呻吟,不如不写。结果还是写了。我想记录这件事,也想借此捋清思路。写到这里,我想,我捋出来了。
在我每一次询问别人的建议时,他们劝我勇敢一点去做了手术,我有点气,气的是凭什么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,一股劲想把我推着往前走,就不能心疼一下我吗。但当有人试探地提出要么先不做时,我更气,气的是跟我的决定背道而驰。
那么结果已经得到的,我的决定并没有变过——我要做。
好吧,那就是25号了。
医生说盯屏写word四十分钟要歇一歇,现在正好四十分钟了,我得关电脑了。
希望明天醒来的我,只会比现在这一秒做决定的我更勇敢,更酷。
如果没有更勇敢,也没关系。坦诚地爱自己就好了,开心最重要。希望月亮不要再日日夜夜被焦虑和恐惧自我折磨了,只要做到这一点,就已经是最酷的样子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