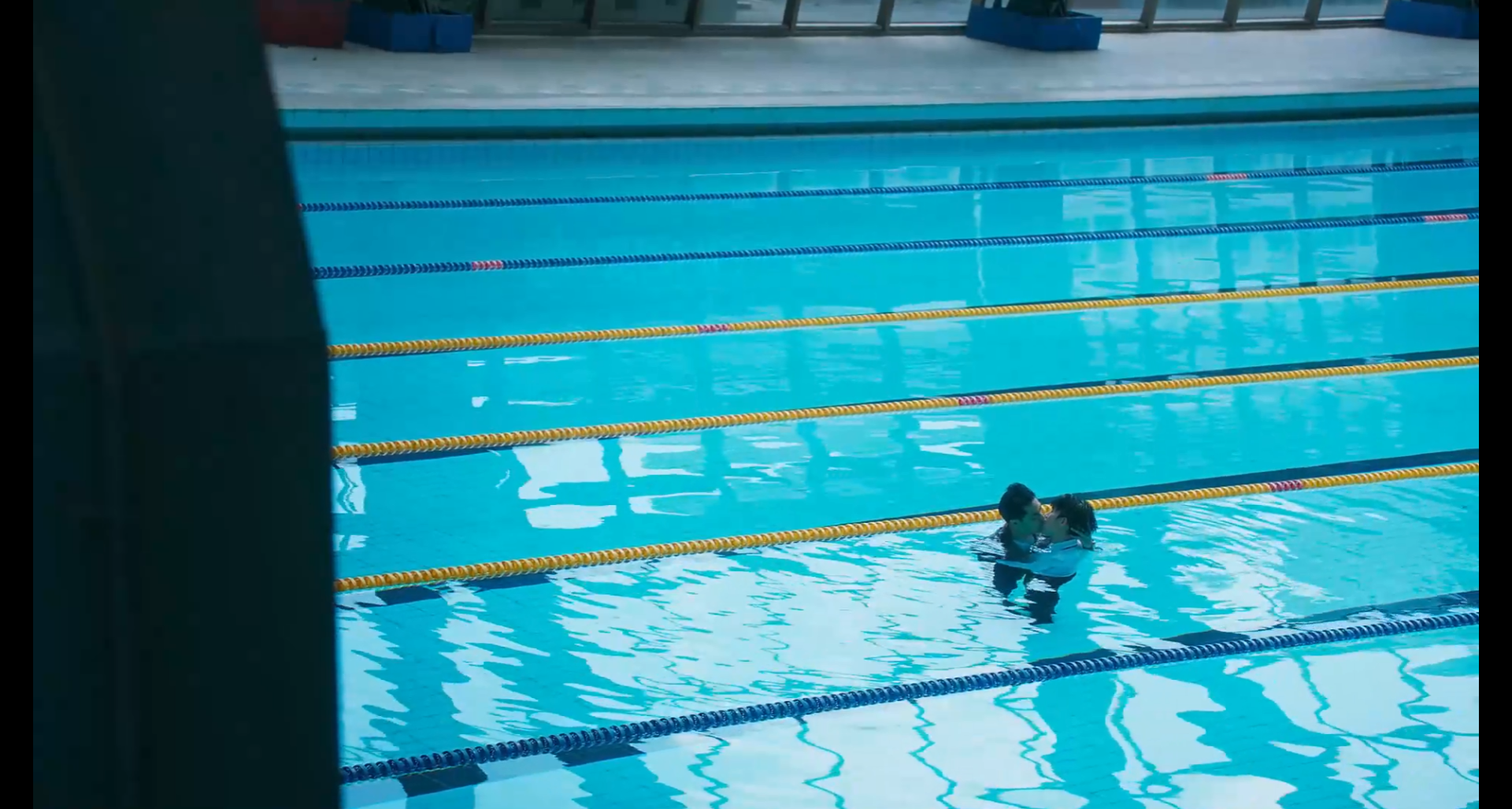《霸王别姬》读后感
一辈子是一辈子。差一年,一个月,一天,一个时辰,都不能算“一辈子”。
原来这句话是出自这里。我以为是表达爱意,原来,是为了告诉读者,蝶衣,是多么爱唱戏,是多么在意这事儿。
他本是六指,六指的小豆子为了能被关师傅收下,为娘的生生剁掉了他这一指,自此,妩媚妖娆,恰到好处的兰花指,大红大紫的程蝶衣,皆是他了。
苦,戏班子苦,学艺苦,可一年盼了一年,也就明白娘不会再接小豆子回家了。好在,师兄弟们大体上是和善的,共苦,总是比同甘容易得多。另外,又有小石头护着,老天爷赏饭吃的小豆子,就那样和师兄相互扶持着长大了。
不如意的人太多了,女人可以哭了,孩子可以哭,但堂堂男子,只能假不同的籍口抒泄:轰烈地打喷嚏,凶狠地打哈欠,向无法还手的弱小吼叫。这些汹涌澎湃,自是因为小丈夫,吐气扬眉机会安在?又一生了,只能这样吐吐气吧。生活逼人呀,私底下的失望,恐慌,伤痛。都是手底下孩子不长进,都是下三滥烂泥巴。他的凶悍,盖住一切心事。重重心事,重重的不如意。想当初,自己也是个好角儿呀。
即是师傅,怎能不严苛,何况又在那么个,有本事都难活命、没本事就更不可能活命的年代。关师傅打,关师傅骂,关师傅也是没办法呀。
小豆子一急,捧过小石头的脸,用舌头吸吮他伤口,轻轻暖暖的,从此不疼。
看到这时,我是有多欢喜呀,我以为是贫贱见真情,我以为是双向奔赴,我以为是小石头明白小豆子所有的亲爱,以为全局的悲剧都将是外人给的。
小石头和小豆子刚刚赚了一点点钱时,在胡同口的垃圾堆里遇见过一个女婴:
是一个小女孩呀,红粉粉的小脸,一生下来,给扔进垃圾堆里头,哭死都没人应?末了被大人当成是垃圾,一大捆,捆起扔进河里去。她头发那么软,还是湿的。哭得多凄凉,嗓子都快哑了,人也快没气了。恐怕是饿呀,一定是饿了。
人如草芥。这年代,连善良都不敢善良。自己还活不过来呢。
芳华暗换
——我好喜欢这个词
后来,两人越来越火了,有了新的艺名。段小楼,程蝶衣。
他憨直而用心地,捡起大拳头,捏住一管毛笔,在庙里几桌上,一笔一画地写着,写得最好的,便是一个“小”字。其它的见不得人,只傻乎乎地,欲拳起扔掉。程蝶衣见了,是第一次的签名,便抢过来,自行留住。
后来,这张签名始终被蝶衣留着,存着,放在装头面的箱子里,做以最珍视的宝贝珍藏着。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爱慕,还要再多直白才够呀?
小楼念念不忘:“我唱到紧要关头,有一个窍门,就是两只手交换撑在腰里,帮助提气——。”
蝶衣问:“撑什么地方?”
“腰里。”
蝶衣站他身后伸手来,轻轻按他的腰:“这里?”
小楼浑然不觉他的接触和试探:“不,低一点,是,这里,从这提气一唱,石破天惊,威武有力。”
不由得想起黑泽和安达。他好可爱,我好喜欢。无可救药的喜欢。但是要克制。要拼命克制。我是男的,他也是男的。他会..不喜欢我越矩吧?那些除非有魔法而永远无法说出口的话,那些绝望的自卑。那些烧得眼睛生疼、心也生疼的喜欢。
可是,菊仙出现了。没什么征兆地,出现了。小楼忽然就有了约会,后来,忽然就有了爱人,用菊仙后来的话说,她是他堂堂正正的妻了。
一个婊子,妓院里的婊子,凭什么就可以,凭什么?可她有着做师弟的永远都乞望不来的东西,她是女人,所以堂堂正正。
妒火并没把他烧死。
蝶衣的妒嫉、疯狂、绝望,从未影响过舞台上的事儿。可见,他如此爱唱戏,且奉若神明。
小楼结婚的时候,蝶衣把自己献给了秦四爷。与其说被逼得无路可走,不如说是为了报复,报复师哥的负。又向秦四爷讨了那个价值一百大洋的剑来。犹记儿时,师兄弟在街上初见这剑,小石头满眼的喜欢,和小豆子满眼坚定地说,师兄,我定把它拿来送你。如今,倒是真真送了。
次日,日本兵入城。
一家一家一家,不情不愿,悄无声息,挂上太阳旗。只有蝶衣,无限孤清。外面发生什么事,都抵不过他的“失”。
后来,戏子不值钱,蝶衣再美,也难保清洁,那个年代的那些脏事儿,顺其自然。
崇拜他倾慕他的人,都是错爱。他是谁?——男人把他当作女人,女人把他当作男人。他是谁?
蝶衣和菊仙,算是斗了一辈子,即便在后来被劳改,直至死,这斗,因着对小楼的爱未停息,斗也未曾停息。菊仙后来也无数次,点他:是个男人。不遗余力。菊仙知道,他永远无人知晓的心事。
后来,他们都六十岁了,蝶衣也经人介绍有了妻。平反后的香港再见面,又合唱了一着霸王别姬。彼时的蝶衣已经是个抽巴巴的老头了,风姿不再。劳改、批斗,如今的他只剩九指了。聊天中——
“是,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,真不宽心。”
——蝶衣是这样形容盆儿糕的,那个儿时的小石头答应带小豆子吃的盆儿糕。
流水帐中说到“妓女”,蝶衣急急住嘴。他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提醒,提醒早已忘掉的一切。
小楼眼神一变。
啊他失言了。
蝶衣心头怦然乱跳。他恨自己,很到不得了。
小楼三思:“我想问——”
他要问什么?他终于要问了。
蝶衣无言地望定他。身心泛白。
小楼终于开口:“师弟,我想问问,不我想托你一桩事儿,无论如何,你替我把菊仙的骨灰给找着了,捎来香港,也有个落脚地。好吗?”
蝶衣像被整池的温水淹没了。他恨不得在没听到这话之前,一头淹死在水中,躲进去,永远都不答他。疲倦袭上心头。他坚决不答。
一切都糊涂了,什么都记不起。他过去的辉煌令他今时今日可当上了“艺术指导”;他过去的感情,却是孤注一掷全军覆没。
他坚决不答。
“师弟——”小楼讲得很慢,很艰涩很诚恳:“有句话——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——”
“说吧。”
“我——我和她的事,都过去了。请你——不要怪我!”
小楼竭尽全力把这话讲出来。是的。他要在有生之日,讲出来,否则就没机会。蝶衣吃了一惊。
他是知道的!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!这一个阴险毒辣的人,在这关头,抬抬手就过去了的关头,他把心一横,让一切都揭露了。像那些老干部的万千感慨:“革命革了几十年,一切回到解放前!”
谁愿意面对这样震惊的真相?谁甘心?蝶衣痛恨这次的重逢。否则他往后的日子会因这永恒的秘密而过得跌宕有致。
蝶衣千方百计阻止小楼说下去。
千方百计。
千方百计……
他是知道的!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!
段小楼原来,一直知道程蝶衣的心意。
这比不知道,还悲伤得多得多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