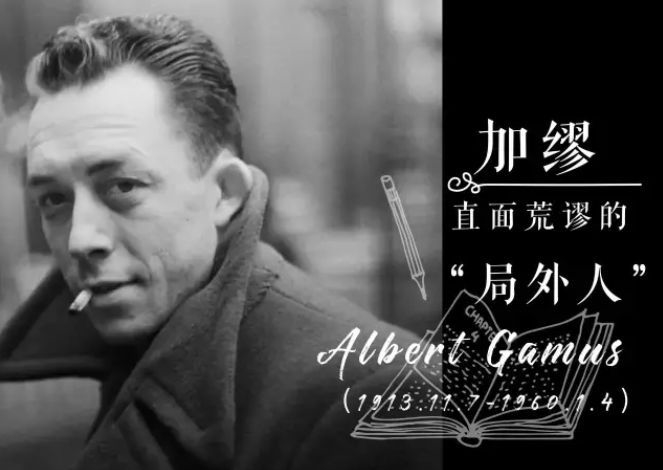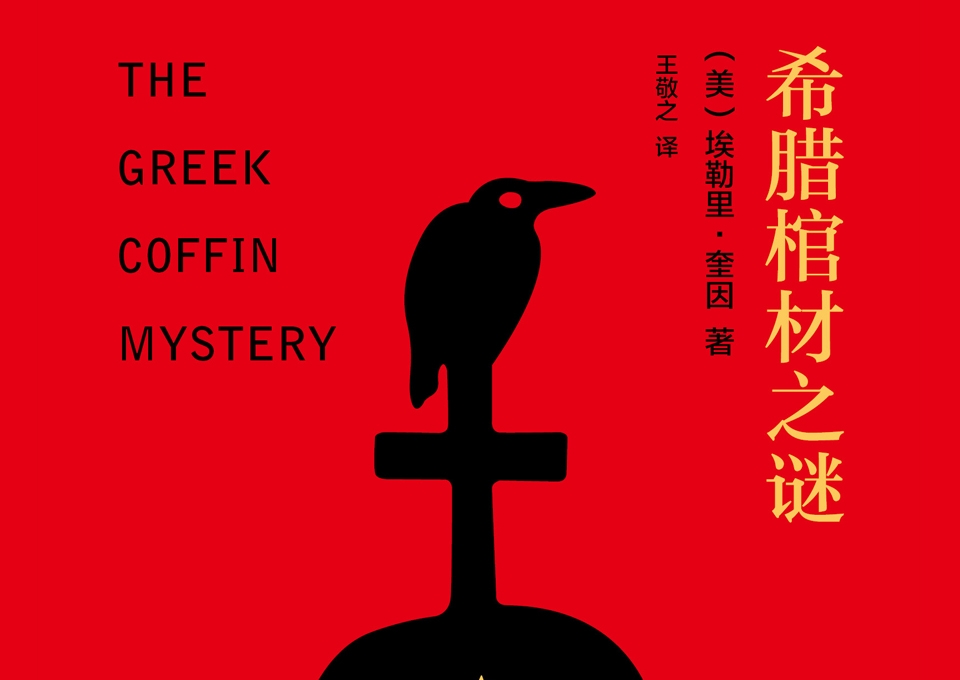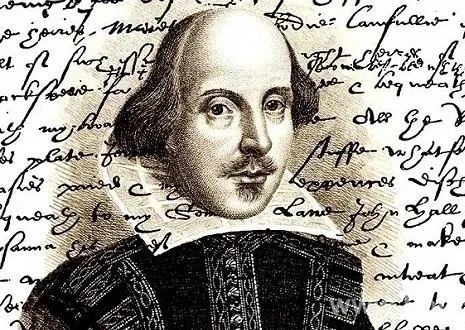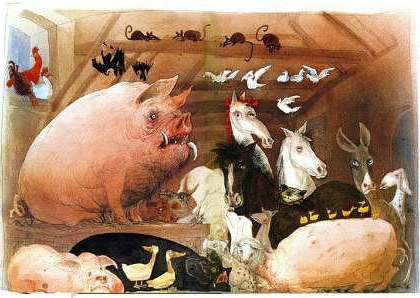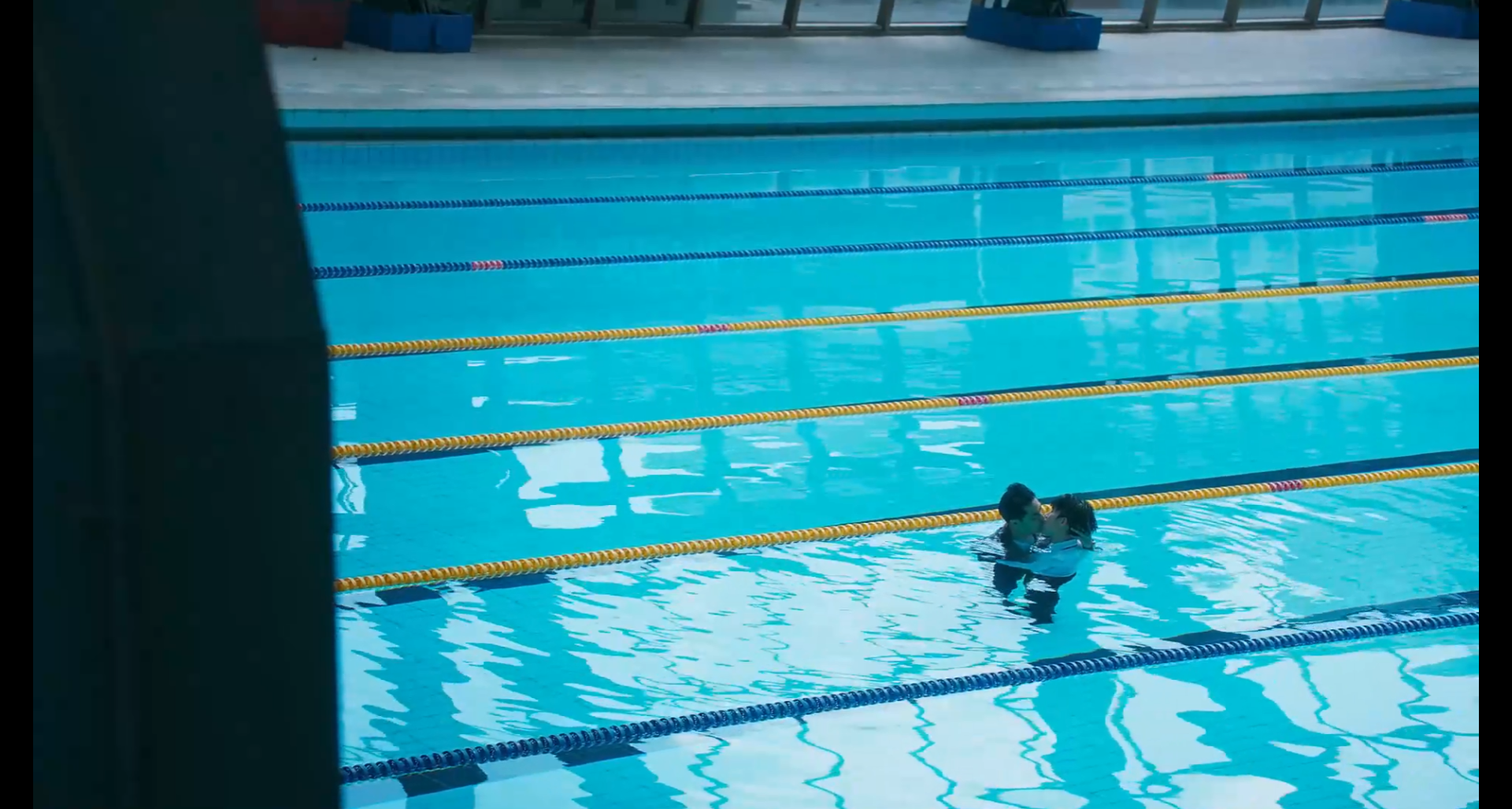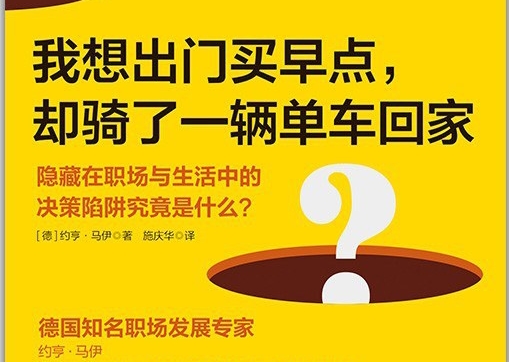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读后感
朋友问我在读什么书,我说,是面对死亡的态度。他生气,让我要好好的。我说,我没事,只是想找个避难所。已经连续了一段时间了,我无法思考,无论是日常的学习,还是一直在日程上的论文,就算是开题也不能让我集中注意。就刚刚,师兄发来消息又催论文了,我应承着。
“很想在一个能晒到太阳的沙发上缩着,看一会书。我想回家了。”我对他说。
我虽死去,福泽绵延。整本书读到最后,保罗的死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胸口,喘不过气,压抑又悲恸。我合上书,戴上耳机,单曲循环加州旅馆,写读后感。
死亡在当今的社会上已经不再是被避而不谈的话题,甚至隔几天就会有相关的事出现在热搜。但是想象发生在自己身上,和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,还是不一样的。保罗当然是勇敢的,人生的辉煌让死亡的打击变得要重于普通人,译者说他坦然又平淡,我明白,相比常理中的反应,确实是足够坦然了。但我总觉得字里行间是夹着恐惧的,他还没活够,还有一万个眷恋,医学上的造诣让他看得明白,却更是绝望。我没有贬义的,这是当然。
追寻生命的意义。如果生命到头来终究一死,终究是渺小至极,那每一分每一秒还有什么意义?那就不管了罢。只需要问自己,此刻做的事情,有没有积极的意义?有没有把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好?每每这样自问,心绪似乎也渐渐澄澈明净,对于死亡的那些虚妄的担忧,也变成了勇敢和笃定。
很多母亲明知胎死腹中,还是要经历分娩和生产。是母爱吧,奇妙又伟大,但只能是,很多母亲,而非所有。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,跟C聊起一点事,他很气愤地说,为什么做父母没有考试,有些人根本就不配做父母。我一边说着,你怎么这么生气,一边心里默默认可着他的话,激起涟漪。
面对绝症,听到消息后,大多数病人都是一言不发。毕竟,英语里的病人,patient这个词,最初的含义之一,就是毫无怨言地承受苦难的人。生病是很奇妙的一个状态。健康的时候,可能有许许多多想要的东西,要财富,要快乐,要爱情,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渴望;可一旦生了病,脑子里想的是:只要能健康,什么都不要了。所以你瞧,在很崩溃的日子里,读一本面对死亡的书,不也像喝了碗鸡汤一般吗。尽管它并没能治愈我。
“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成功却又这么坚持善良美好人性的人。”可即便是如此美好的人,在癌症面前,也难免一死。
海德格尔曾说过,无聊,就是感受到时间的流逝。我想,倒过来是不成立的。去感受时间的流逝,可并不无聊。
在治疗的日子里,保罗一次次提及“希望”这个词。面对绝症,也只能赌一场希望了吧。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,大概1000年前出现,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。可保罗渴望的是活下去,有信心的却是死亡,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啊。这多令人心疼难过啊。
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。我说,你给的,那我就受着。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: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。没有痛苦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没有条纹的老虎。痛苦如果一定要来,逃不掉的。
勇敢就是如此吧,不确定结果,却依然敢坦诚面对,将来的事,谁说的准呢。就像电视剧里总是演,男主角或者女主角会在故事的开始跟朋友讲,将来谁要是跟那个人在一起,一定是脑子坏掉了。这种话一出,你看着吧,故事的结局一定是他跟那个人在一起了。对,生活不是电视剧。但是既然被告知白血病的故事都能从电视剧跳在我身上,那我最期待的幸运一定也可以。
我们要继续活着,而不是等死。